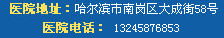虽然历史记载,西周初期出现了“成康之治”的鼎盛期,但是实际上并不太平,戎狄蛮夷交侵。周人之所以对他们蔑称还与之有战事,无非是在周人的“自我中心”及狭隘民族观之下由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、生活方式不同、意识形态不同以及争夺生存空间导致的冲突。
(见周朝与邻居——戎狄蛮夷的爱恨情仇)而南蛮楚国与姬周也有矛盾,而且还另有原因。
传世文献中,楚先祖可追溯至五帝时的祝融族,商朝中期时受到商王室的打击,商末时楚国几乎与姬周同时建国(见悲催的楚人在商朝末期被商、周联手赶到了南方),周、楚两族的族长周文王与鬻熊往来密切:《左传·襄公十四年》载楚武王说“吾先鬻熊,文王之师也”,史记·楚世家》称“鬻熊子事文王”;先周遗址周原甲骨卜辞有“曰今秋楚子来告父后”、“楚白(伯)乞(迄)今秋来即于王其则”等,“楚子”“楚伯”可能就是鬻熊。周初时,楚人接待了从宗周逃难的周公(见周公当政七年后还政成王:不得不说的权斗内幕)。周成王承认了楚人的政权并以之作为周王朝的伙伴(见为何要考编制:成、康“并建母弟”与周朝第三次分封)。西周早期“生史簋”铭文载“召伯令生史使于楚,伯赐宾(或赏)”,一说“伯赐宾”指召伯将楚君赠送使节之礼物赐给生史,二说是邵伯赏赐了生史。总之,西周早期很可能是成、康在位时派使臣沟通楚国。“荆子鼎”铭文称“荆子蔑历”,“王赏多邦伯,荆子丽”,有学者认为“荆子”即“楚子”即熊绎。如果所说属实的话,可证成(康)王时周、楚互相往来聘问,说明关系不错。如此楚国加入了周天子、周礼这个联合国体系,周天子所谓王土也南延且有一方诸侯坐镇。然而数十年之后,两国便兵戎相见,而且整个周朝时期,楚国都不服从周王室。史书记载周康王儿子在位时南征甚至丧命于楚;周夷王时楚人开始撇开周王自称为王,周厉王时因畏惧才去掉王号;周宣王时多次伐楚;东周时期楚人再度称王,还扬言去洛阳观看周鼎——即炫耀能耐。据称,湖北等地把不服、不服气等说成“不服周”就是因此。
友谊的小船怎么说翻就翻?楚人为何对周王朝不满?
这可能来源于三方面。
一是楚人被迫南迁。
按《史记·周本纪》,周成王分封楚国时,“封以子男之田,姓琇(即芈,金文作嬭)氏,居丹阳”。汉代以来便以丹阳为楚国最早的都城,然而后人考察丹阳地望,产生今安徽省马鞍山市当涂县、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、枝江市(宜昌市的县级市)、丹水和淅水交汇处的今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、丹江口市,后又有今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等多种说法。“当涂说”最不靠谱,最早被抛弃;“秭归说”也逐渐被否定;目前最主要的、争议最大是各有文献及考古证据支撑“南系”——“枝江说”和“北系”——“丹淅(淅川)说”以及“中系”——“南漳说”,但是三说也各有欠缺,无法定论。石泉《楚都丹阳地位新探》又提出熊绎的丹阳在丹水源头处今陕西省商洛市区的“商洛说”,因此该地区有很多以名作荆、楚的山、川;随后由丹水南下至今丹江水库附近即淅川,但是具体时间不明,至少周夷王之前,或是周昭王南伐之时。
实际上,并非熊绎才居丹阳,《世本》说“鬻熊居丹阳”,也即熊绎的太爷爷就已经居住在丹阳了。此说具有很高的价值,因为在说熊绎的楚都时,不能忽视其先祖的旧居地。鬻熊作为一个楚族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,一定有一定的势力范围和政治中心。《世本》说他“居丹阳”是因熊绎建都于丹阳而追溯其祖也居丹阳,还是他本居丹阳?鬻熊和熊绎在同一个丹阳吗?
其实“丹阳”最初的意思的“丹水之阳(水北为阳)”,丹江北岸都可以称作丹阳,所以楚人不论在哪主要是在丹江北都可叫丹阳。甚至离开丹江,新地也可叫丹阳,比如后世的“郢”,楚人迁都后新都都叫郢,外国也有这种习惯,欧洲人跑到美洲后给新地取名为:新约克(NewYork,今译纽约)、新奥尔良(NewOrleans)、新泽西(NewJersey)、新罕布什尔(NewHampshire)、新英格兰(NewEngland)等。
很可能鬻熊的丹阳和熊绎的丹阳不同,也即鬻熊以来熊丽、熊狂与熊绎的楚都不同。
这一点,出土文献清华简《楚居》可证:季连后期迁“京宗”;到穴酓(鬻熊)时“迟徙于京宗”;“至熊狂亦居京宗”;“至熊绎与屈紃,使鄀嗌卜卜徙于夷屯”,反映出鬻熊、熊丽、熊狂及熊绎四代都在一地,而熊绎后来迁都了。
《左传·昭公十二年》又载“昔我先王熊绎,辟在荆山”。《墨子·非攻下》说“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”,即开发睢山一带。无独有偶,出土文献长沙马王堆西汉帛书《战国纵横家书》载“楚将不出雎、章”,河南省新蔡葛陵故城楚墓竹简载楚人追述“昔我先……宅兹雎、章”。《左传·哀公六年》记楚昭王说“三代命祀,祭不越望,江汉沮漳,楚之望也”,望是一种祭祀方式,《尚书·尧典》载“望于山川”,即祭祀山川,这句话表明楚族龙兴之地在“江汉沮漳”。都认为楚人曾在雎、章一带创业。
暂不论熊绎的丹阳是在丹淅、南漳还是枝江,先看商末周初时熊绎受周成王分封前的楚国都城在哪。
分析以上资料,最重要的信息有:(1)《楚居》认为鬻熊、熊丽、熊狂都在京宗,熊绎徙夷屯;(2)鬻熊、熊绎都居丹阳,当然他们中间的两代熊丽、熊狂也当居丹阳;(3)楚人最初的活动范围的地理信息包含荆山、长江、汉江以及名为沮(雎)、漳(章)的山或川等地方。
实际上,(3)是一个整体概念,反映的是楚人艰苦奋斗后打下的一个稳定的根据地。所以,最主要的是京宗与夷屯也即两个丹阳的区别。
京宗与夷屯也即两个丹阳当是相距很远,楚人在熊绎受封以前应该很接近宗周、中原:
不论是文献记载还是周原甲骨卜辞关于商末楚、周的往来事迹,都说明鬻熊与周文王往来密切。西周初期周成王怀疑周公,周公害怕被杀,逃到楚。当时的楚地距离宗周、成周不会太近,但也不会太远:因为太近的话成王就会派出数百轻兵足够追杀。(而且楚人当时势力还算强,因为他们当时还不完全属于周,如果势力小的话保护不了周公。)而周公年纪大了,跑太远可能死到南路,而且他还想着大侄子能回心转意接他回去继续享受荣华富贵呢,肯定不会跑远。
古代交通不便,从商末、周初楚、周的交往来说,那时的楚距离姬周的中心岐丰即今陕西省西安市应不远,否则两族不可能往来密切。所以,楚人在商末周初的中心应该尚且靠近中原,或许就是商洛,最远不过淅川。
而据《左传·昭公十二年》楚人追忆先王熊绎“辟在荆山,筚路蓝缕,以处草莽”,辟不论解释为躲避还是偏僻,都有愤恨的意味,张正明《楚都辨》说“带着抱怨甚至诉苦的口吻”。这说明,熊绎迫于某种压力离开故地、向外围远迁。应当是夷屯、熊绎新的丹阳或荆山距离京宗、旧丹阳会有相当距离,不然也不会沉痛于熊绎“筚路蓝缕,以处草莽”的创业艰辛,及《楚居》所载宗庙建成后连祭祀的牛都没有结果偷人家的牛为牺牲的“鄀国盗牛”丑事。
总之,无论传统文献中丹阳地望在何处,结合“卜徙夷屯”、“辟在荆山”等各种因素,都说明熊绎重建楚国时迁都了;至于丹阳的地望,无论哪种说法,都比较靠南,所以是南迁!很多学者都认同楚人迁都,或认为从顺着丹江南下由商洛迁至丹淅,或认为从丹淅徙至南漳,可能也可能由丹淅迁至枝江,新的都城依然名为丹阳。
熊绎迫于何种压力南迁呢?
(1)被周成王摆了一道
如果认为丹阳即夷屯,那就是熊绎受封时迁都的,可能因为楚族加入姬周同盟圈时被成王摆了一道。
《楚世家》载周成王“封以子男之田”、“乃以子男田令(熊绎)居楚”。但是,(1)周分封楚,实际是对楚国的法统再确认,即吸收进“联合国”;(2)周朝(至少周初)根本不存在所谓“五等爵”制,《孟子·万章下》《礼记·王制》等所载子、男之田五十里,实际上是周人限制“异族”发展的策略,即只有我姬周宗室诸侯国才可以有通都大邑,你们“异族”方国,只配或者只允许你五十里,不可以过度发展以坐大(见周朝的封建制及爵位制不是书中记载及你想象的那样)。其实这是一桩对楚国更有利的买卖,抱住姬周王朝的大腿,能和平与姬周各国做生意,互相交流学习,融入大趋势,享受强大姬周经济、社会、科技发展的“溢出效应”。但是对周来说未必,周人可能因此而显示仁德,或者名义上成为天下之主,但是周人不差楚族这个诸侯,或许也能趁势灭其国。而且作为与姬周几乎同时兴起的一大部族,姬周对楚人在卧榻之侧鼾睡很不放心。
所以,姬周“分封”熊绎即把楚人加入周王朝的“联合国”并不是没有条件的。楚人要加入周王朝“体制”,那么必须要服从姬周的安排,投大哥除了要交保护费——定期朝、贡,而且还要纳投名状!
所以,双方互相妥协:姬周承认楚为大周“联合国”的成员国,即周人承认楚人政权的存在,楚人尊周为宗主。而楚人接受姬周统治的现实,不能产生威胁,还要迁都到更南的地方,把商洛或淅川一带让出来,也不能过度发展,减轻姬周在南路的压力,还要作为王土的南端,威慑其他异族——这就是楚人纳的投名状!
(2)后来受到不公待遇
当然丹阳与夷屯也许不可画等号,也可能是后来成王或康王时受到不公平对待,熊绎一怒之下迁走了。
总之,在周成王承认楚国、允许其加入姬周“联合国”时或其后,楚人南迁了,但一定不是自愿而是被逼无奈。
二是周成王时受到鄙视。
对于刚刚受到分封的熊绎应该说,楚国虽然做出了让步,但是与南迁相比是划算的,所以获得周天子体制还是比较激动的,就像是一个家本在市区的孩子,虽然考到了距离市区百公里外的县城公务员或者编制——总算是进体制内了呀。
数年后,周成王一声令下要会盟诸侯。熊绎异常兴奋,终于可以到京都去了,终于可以再见中原的繁华了,因此不顾贫穷,不顾路程遥远,率领一群人架着装满桃弧、棘矢、包茅的车,千里迢迢去了大西周。
《国语·晋语八》称“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,楚为荆蛮,置茅蕝,设望表,与鲜卑守燎,故不与盟”,结果熊绎到了那里,周成王认为楚人是蛮夷,没有会盟资格,不让他以诸侯国君的身份参加正式会议,估计又认为其先祖祝融是火正,就让他与鲜卑一起“火寮”,就是举行会盟时负责篝火。
可能熊绎也不含糊,满口答应了。
现代火电厂是是一套自动化系统,提前设定的程序会自动添煤,有异常情况会发出警报,甚至能自动处理。负责这一块的工作人员只要悠闲的喝喝茶看着系统运行即可,而电厂工资很高又多是另外羡慕的大企业,你羡慕他们时,这些工作人员一边傲娇一边自嘲说“哪有,我就是烧锅炉的”。
熊绎估计有这种心理,既有失落感,又有优越感,毕竟对底层人来说能够“烧锅炉”服侍上封也是一种荣耀,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。而且周天子让熊绎守火,或许是因为先祖祝融是火正,祖上传下来的手艺,所以做火寮也没什么。
后来诸侯正式会盟,其他君主都是主角,和周天子互相敬礼,而熊绎却只能端酒、倒水、烧火——竟然不能参与盟会。
熊绎觉得不对劲,有些失落。而且时代不同了啊,当年守火是光荣的职业,现在人们用火已经常态化,再守火真是烧锅炉的了。
我是来干啥的?熊绎内心隐隐升起来了悲痛:不对啊,咱是代表一个国来参加会盟,怎么成了“服务人员”,让我烧锅炉了?
但是熊绎不敢表现出不满,依然认真负责,锅炉烧的很好。成王一高兴,哈哈,那你以后就继续烧下去吧。
三是周康王的继续漠视。
《左传·昭公十二年》楚灵王对其令尹子革说“昔我先王熊绎,与吕伋、王孙牟、燮父、禽父并事康王,四国皆有分,我独无有”,《史记·楚世家》解释为“齐、晋、鲁、卫,其封皆受宝器,我独不”,意思是,周康王即位后,姜太公传人、齐国第二任君主吕伋,卫康叔儿子、卫国第二代君主王孙牟(《史记·卫康叔世家》称“康伯”《世本》载“康伯名髡”),晋国君主燮以及鲁国君主伯禽与楚熊绎一起服侍周康王,但是后来,周康王赏赐了四人国宝重器,唯独没有给熊绎。
子革对楚灵王解释说“齐国女儿嫁给周天子,是周天子的舅父;晋、鲁、卫都是周王室的宗族子弟。而我们楚国与周天子有什么密切关系呢?所以,他们四人受到周康王的特殊对待而没有分给楚国宝器,又有什么不可的呢?”子革的解释已经很令人释怀了,人家鲁、卫、晋是周天子同宗,还没出五服呢,而齐是大功臣又有联姻,而楚国跟周天子关系比较疏远。
但是楚灵王对周王室的不满并非一日形成的,很可能那时熊绎感觉一万点暴击,想进却进不了圈子的挫败感悠然而来,又想起来当年烧锅炉的事了(康王也有“丰宫之朝”,可能举办那次大会时,熊绎也免不了烧锅炉),内心失衡了,“去TMD锅炉”“去TMD的国宝重器”“去TMD的周天子”,内心不平,开始憎恨周国和周天子,以至于流传下去,楚国历代各君都对此事念念不忘。
所以,三件事:(1)成王逼迫熊绎南迁,(2)成王岐阳之蒐让人家一国之君烧锅炉,(3)康王赏赐一同服侍他的诸侯国君财物唯把熊绎落下啦,使得楚国心灰意冷——融不进的圈子不强融,开始疏远周王朝。
很可能自熊绎后期也即周康王后期,因熊绎愤恨开始不进贡不朝见,甚至屡屡与姬周作对,拉开了“不服周”的大幕,甚至导致后来康王之子周昭王的征伐。
当然,抛开历史表面化的记载,楚、周矛盾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楚在江南要独立发展,而周人希望楚人听话,甚至将其收入麾下,但又要抑制其发展,而楚人不希望姬周及其在江南的诸姬掣肘。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abmjc.com/zcmbzz/9346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