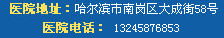1
在年,一位老人背着一张桃花树的照片,深深触动了许多中国人的内心。
移民背负着桃树
十年前,他成为了三峡库区的移民。他穿着解放鞋,背着这棵桃花,在屋檐下静默了很长时间,最后含着眼泪走上了一条完全陌生的道路。
刘敏华,是北秭归县郭家坝镇的一个山区居民。
然而,这张照片所隐藏的事实是,还有超过一百万人与他一样经历了搬迁。
每一幅画面都在述说着历史的流转与无法言说的苦涩...
2
在年3月,摄影师李风来到了三峡的两岸。
当我经过三峡大坝时,在秭归县郭家坝镇遇到了李敏华。
在那时,李敏华所租住的房屋已经被确定为三峡库区的搬迁范围之内。他拿着满满的包裹,正准备搬迁到远离的新家。
最后,他无法割舍门前那棵桃树,于是将其从土地里挖出来,装进背篓背在身上。
李风捧起相机,记录了这个场景。
门前的桃树
自年以来,李风面对着三峡和三峡移民,他已经拍摄了无数张照片,而这张名为“背起桃树的移民”的照片一直保存在他的电脑中。
直到年,《中国国家地理》在制作湖北特辑时向他请教,这张照片才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巨大的讨论风潮。
年4月份开始,三峡工程被誉为一项规模庞大、任务艰巨的工程,其移民规模堪称巨大。
该地区也是最大的水库淹没区域,这就意味着将有平方公里的陆地被水淹没,其中包括两座城市和十一个县城。
自那时起,约有万人带着对未来的美好期望开始了迁徙生活。
移民
他们离开了自己的故乡,分别去了上海、北京、重庆等不同的城市。
每个人都说搬迁是从固态到液态的积极变化,但是居民们总是感受到一种说不出的伤感。
在当时的摄影界,主要以拍摄风景为主题,很多摄影师都把他们的镜头对准了美丽的三峡,拍摄出了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作品。然而,唯独李风选择了将他的镜头转向了三峡的移民群体。
他表示:“我一直觉得他们身上带有一种强大的力量,那是一种平凡而又闪耀的东西。”
在过去的千百年中,三峡一直是无数中国人的心头所向,许多文人也曾为三峡创作了独具美感的诗词作品。
在20世纪末,它再次成为了一座闪耀的地标,通过一项伟大的工程,这里将焕然一新。
当时的情况是,库区水位需要按计划上升到米,也就是说,地势低于米的地方都将被淹没。
包含居民的家族住宅、历史遗迹和一切珍贵的回忆。
标识高度为米。
李风看到它们即将消失,心中不忍,于是他毅然决定辞去工作来到了三峡。在过去的27年里,他用相机记录了无数美好瞬间,每一张照片都令人回味无穷。
我在江边长大,有时候看着他们,感觉仿佛重见了童年的自己。
其实,在搬迁和改革的背后,一直隐藏着我们无法察觉的事物...
3
李风于年在湖北恩施出生,他们一家是合法的移民。
他的父亲原本是从武汉调到恩施的,随着文革的到来,他邂逅了一位来自贵州逃难的李风的母亲。
恩施当时是个远离城市的偏僻地方,却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汇聚在这里。
我们曾经住在文工团,里面聚集了许多有趣的人。
根据李风的说法,他的邻居有一位教英语和教哲学的老师,还有一位专门绘制海报的老先生,这位老先生是从湖北美术学院调到这里的。
他们常常聚集在一起,就像一个团结的大家庭一样。
然而,随着文革的结束,大约在年,所有的人都突然离开了。
院子
为了生活和家庭的原因,他们各自选择去了不同的地方,有些人外出打工,有些人选择返乡。
在这里有一对夫妻,在离开之前他们离了婚,原因是妻子渴望留在恩施,而丈夫则有意去其他地方发展。
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,孩子们一个个被分开,一个家庭就这样瓦解了。
在李风和他父亲去送那个叔叔时,一辆汽车刚一鸣笛,他的儿子就从窗户上跳下来,表示不愿意继续前行。
没有人能够预测他们接下来的命运和发展方向。
随后,李风一家也决定搬到宜昌去。母亲和父亲早早地整理好了家里的物品,房子刹那间变得空荡荡的。
他清楚地回忆着在恩施度过的最后一个晚上:邻居们一个接一个地邀请他们到家里吃饭,大家都在互相道别。
他当晚躺在地上,身体下放着一张凉席,整夜无法入眠。
移民
第二天早晨,他们租了一辆绿色货车,李风提着行李,扛着凉席,跟着父母离开了恩施。
在那个时候,宜昌还没有建造跨江的大桥。所以他们在途中下车,然后乘船到达了他们的新家。
我第一次搬家,感到非常困惑,无法言喻。
后来他进入了湖北大学,在那里学习了财会专业,然而他对摄影却有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热情。
“我发现很多国内外的摄影作品都在拍摄三峡,而我的家就在三峡的出口,因此我感到非常自豪。”
年,李风购买了一台海鸥相机,像其他摄影师一样,他开始拍摄三峡的风光。
他的改变始于偶然穿过巷子时,无意中目睹了一群"挑夫"。
挑夫
挑夫的工作是为人们打包物品,然后用担子将其送到车站。当时,他刚从三峡附近回来,恰好看到他们正在用凉水沐浴。
他们家就在他们的身后,是一个20平米的大房子,里面住着一家人。床是摞成一层一层的那种,看起来非常拥挤。
自那时起,李风的头脑里一直闪现着一个念头:
到底我们应该拍摄人物,还是风景呢?真实的中国究竟是怎样的?
如今来看,这个问题早已得到了解答,但在过去的时代并不受欢迎。
在夏天的一天,具体来说是年,李风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。他将摄像机的焦点对准了三峡移民,然后按下了快门,拍下了他的第一张照片。
真是巧合,那一天中午他恰好碰上了送移民的小船,一个大概10岁左右的男孩正在背着凉席朝着岸边走去。
当时,我立刻联想到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。
一个抵御寒冷的男孩
我不知道小男孩是否也会有和他一样的困惑。听说他的新家在坝上库首,那是距离大坝最近的一个村庄。
在询问了一番之后,李风了解到这是第一批移民,而三峡百万人口的大规模迁徙也由此开始。
4
“一旦我拍摄到了那个小男孩,我就明确知道应该拍摄些什么了。”
李风在三峡逗留了三周的时间,在那段时间里,他成功地拍摄到了一个刚出生14天的婴儿,这个婴儿正与家人一起搬迁到了湖南。
她的妈妈穿着一件蓝色的衬衫,伞压得很低,背着一个竹框,带着她走在前面,后面还有几个戴着鸭舌帽的年轻人。
这个女孩的名字是“李庆迁”,表示对三峡改革的庆祝。然而,她的母亲却不情愿地说道:
“看来未来只能向孩子讲述她的出生地了。”
搬迁的速度非常快,所有事情都按照预定的时间表进行,甚至连白帝城的邮局都已经拆除,只留下门前的那棵大树,树上挂着一个邮箱筒。
树下的邮筒
巫山的码头被封闭了,渔夫们熟悉的标志也不见了,唯有一个红漆写的标语“请到此处乘船”依然存在原地。
在年,当三峡大坝开始蓄水的那一天,李风从宜昌出发前往瞿塘峡的途中,遇到了一个男子。这位男子非常友善地为李风指引了一条近路。
由于他缺乏教育和社会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abmjc.com/zcmbwh/8846.html